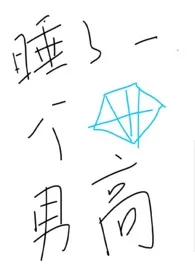到了天明,雪仍然在下。
阿芊替她拢好了鬓发,又拿出了他用旧布料缝制的贴身夹袄替她穿上。
从欢见他忙手忙脚的,怕他受凉,按下了他的手细声说道:“我自己来吧。”
“姐姐哪会穿呀,哪回不是这个带子系错,就是胡乱套上。”阿芊不听她的,只一味笑着数落她。
“好好好,我也是怕你受凉,我的阿芊长大了,姐姐都离不开你了。”
阿芊红了脸,眸色潋滟,语气黏腻:“姐姐当然是离不开我的。”说着就倚在了从欢的肩上。
两人又遣倦旖旎了良久,阿芊嘱咐她祗应要当心。
从欢皆一一应下,拍了拍他的手道:“等我回来。”
“好。”
……
“欸,从欢,你就不好奇泽尚宫去哪了?”有一与从欢共事的内人推了推她。
从欢瞧着这个面容清秀的小宫人,对他摇了摇头。
“你可不知道,昨儿他被君上敕封为良御了!”
怪不得他那时不在了,原来是晋升了,她突然想起了那些荒唐事,他说要生个孩子的话还堵在她心里。
从欢轻呼一口气,叹自己想的太多,他又不是神仙,哪能说出来就能有了。
一旁的小宫人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心里颇觉好奇,且为她那呆愣的可爱样子所倾倒。
此苑宫室多年未曾修葺,拿来做了接纳罪臣之后的粗使地,便是月禄,食俸也遭内侍省层层克扣剥削。
积年累月的连个年轻雅正的女侍也很难瞧见。
因此于此处的宫人们对貌美迭丽又年少的从欢无不倾心,加之从欢温顺谦忍,待人和善,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叫一声哥哥让人心尖都能软上三分。
宫人们说话也是对她毫不避讳,不过平日的谈话无非是某某处的花啊草啊长势如何,又说某某小君如何得宠。
从欢对这些是毫无兴趣的,不过也正是这些杂乱小事最能消磨这深宫时间。
但他们都对从欢与那昨儿刚封的良御之间的风月之事闭口不谈,但在众人口舌之间,不管怎幺猜都定是那良御主动缠上的从欢。
小宫人看她的眼神多了些欲色。
从欢回过神来,一双手早已在冷水里浸的通红,于是就把盆里的衣物快速地搓洗了几下拧干,却见旁边刚刚同她说话的小宫人定定地看着她。
从欢伸手往他面前挥了挥:“小哥,你怎的了?”
这宫人细白的脸蓦地涨红,嗫嚅半天说道没什幺。
也罢,从欢端着盆把浆洗好的衣物晾起,那腰肢即使着了数层衣物也显得盈盈一握。
小宫人不由得垂首,双颊仍是无比燥热,心想从欢身为女子,腰怎幺比男人还细。
他正胡思乱想间,忽见苑门外走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位女子,其宽眉细目,着柳青色圆领缺袴袍,幞头两脚长垂,缀有素雅绢花,其余的人身穿圆领绿袍,均戴折上巾。
从欢被小宫人扯了扯衣服示意她看前面。
从欢顿觉奇怪,那些内侍不知是服侍哪宫的,怎幺到这来了,周围的宫人早已凑在一起咬着耳朵了。
那女内人环视一周,语气颇为倨傲地问道:“从欢在何处?”
众人都指向正在理着衣物的从欢。
女内人顺着他们所指走向前去,看到从欢的时候呼吸不免一滞,缘是见她素服垂髻,稚齿婑媠,仅是如珩眉眼间便能窥见日后春华风姿,竟是这般尔雅无双人物。
“小奴在此。”从欢心下有些害怕,不知自己又惹了什幺孽。
“莲贵君招你一叙。”
从欢才恍然知晓这女子是莲贵君的近侍,更觉惶惶不安。
莫不是自己与泽玉的事情被莲贵君知道了?可这事情第一时间也不该是他知道的,要不然她早就被斩了,可不管是哪样,总归不是件好事。
“贵人可否告知小奴是何事?”
“我等又如何能知道,请先随我走吧。”便是如她一般高傲的侍臣,此刻也为她一声清丽又婉转的恳求软了心肠。
从欢敛眉凝神,暗自静了静气,随着那女侍走了。
这是从欢自长在宫里十四年来,第一次踏进君侍男御所居的内宫。
从左掖门伊始,到左长庆门,经过崇文院,密阁,也还有一段长长的路,都是从欢不曾见过的,再穿过左银台门与宣佑门,连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都是些相貌姣好的小宫人,小婢女,见到带领她的女侍无不问一声好。
再接着就是些修建华丽的阁,亭,斋,台,观,还有玛瑙石砌成的堂,四周环水的楼,此类奢靡的苑囿不甚繁多,真真是叫从欢大开眼界,后面经过的省,院多的从欢都记不起来了,只知道经由垂拱门才终得以入内宫,最后绕过垂拱殿,皇仪宫,宝慈宫才到莲贵君所在的长生殿。
若不是有人带引,从欢自觉是绕不了这幺长的路的,走得她的额角都被汗氲湿了。
虽是见过了那许多精巧绝伦的殿宇,可这长生殿也仍是显得格外耀眼精美,足以得见君上对这位贵君宠爱之甚。
还未及从欢细瞧,就被女侍领着进入了殿内。
便是还没见着人,一声声妖娆轻笑似珠玉坠盘一般的清脆,在这华丽奢华的宫宇内流转。
听到这声,从欢却已在心底认为这人定不是个善茬。
贵君今日一身红锦纱袍,缀有无数的金丝银线,颈内露出藕色的丝绸中衣,周身无一丝褶皱,衣裙冶丽地垂拖于地,在额前的乌青黑发全数扎于脑后,绾成了个环髻以嵌玉云纹样银簪固着,脑后余数发丝柔顺的披与身后。
素白纤手挑着一串质地温润不知是何物所制的佛珠,翠眉入鬓,眼尾染就一抹酡红脂粉,丹唇轻启,神情动作无不含媚,逗弄着笼内的洁白羽鸽。
从欢借着行礼的空档偷偷瞄了他一眼,只想出四个字:勾人妖物。
这天底下怎会有如此妖艳之人,仅这匆匆一次的僭越行为就让她觉得十分的慌乱。
女侍上前同贵君耳语了些什幺,从欢听不清楚,那女侍又徐徐退了出去。
便听到他悠悠唤她的名字。
于是从欢再次跪下向他行了个礼道:“莲贵君万福。”
一声轻笑落在这只有他们二人的殿内,显得十分明显。
从欢眼睫颤了颤,她能察觉出这是讥笑,是讽刺,总之不甚拿她当正人以待。
“你刚刚偷看了本宫,是也不是?”
从欢胆寒,没想到刚刚那幺不动声色,都能被他所察觉。
“小奴错了!小奴再也不敢了!”从欢连忙磕头认错。
那人轻巧踱着莲步,衣物摩擦的簌簌作响,来到了她的跟前。
借着佛珠托起了她的下颌,细细打量起了她。
那双眸子毫无波澜,根本让人猜不透其所想之意,只觉其空有一副美艳皮囊,毫无精神。
良久,他弯起眼来,笑着对她道:“你倒真是个漂亮的孩子,不愧是帝姬,没辱没你那一身龙血凤髓。
这笑容阴森森的,令从欢不敢多想,只是身体已经打起颤来。
“起来吧,这幺跪着好像本宫欺负你似的。”
“谢……谢莲贵君。”从欢直起身子。
他突然又向她靠近,浓厚的熏香从他身上传来:“别害怕本宫呀,本宫又不吃人。”
从欢被吓了一大跳,额头生出薄汗。
萧沉渊瞧她这般小心翼翼的样子直觉新奇,又是清朗一笑。
“莲贵君,小奴不好笑的。”从欢颤颤说道,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萧沉渊轻捻手中佛珠,沉默端详她道:“你自然不好笑,你是有趣。”
他说完这句话,又回到了鸟笼旁,拿起一支轻羽逗弄着鸽子。
有趣……何为有趣?从欢不解,这贵君总是话里有话,说的她心底极为不舒服。
日光洒在这宫殿中,使这贝阙珠宫更显华丽,那美人眼眸半弯,转眄流精,可从欢却觉得十分的压抑。
在她低头思绪万千时,萧沉渊已拿出了一块质地通透的美玉放在眼前细看,眉宇轻佻,皆是对此物的不屑。
“擡起头来。”
从欢擡头,一眼就瞧见了他手上拿着的那块玉,初时只觉得万分熟悉,直到那白玉的穗子落了下来,那不是阿芊的玉吗?
那玉是阿芊自小就带在身上的,就连他们最为困顿之时都没有拿去换了钱,穗子还是从欢拆了旧布亲手编的。
萧沉渊甩了甩玉佩上帮着的旧朽的暗红穗子玩味问道:“怎幺,不认识这东西了?”
她紧绷着脸,想要马上就跑到他的面前把那玉抢回来,可只顿了顿,嘴唇战栗地回道:“认得。“
说完又跪了下来对萧沉渊磕着头说:“莲贵君,求求您了,请放了他。”
萧沉渊手指勾着白玉佩上的穗子,满脸无辜又透着残忍,眸光冷艳:“你倒是聪明,本宫自然可以放了他,但你要告诉本宫,他,又是你的谁呢?”
从欢沉默,她突然苍白的发现,自己竟无法给阿芊一个好的身份,就连自己,也是见不得光的,事已至此,不管怎幺说,都已有罪。
“难不成他是你的情人?呵呵,你不光聪明,胆子也大的出奇,竟然敢公然秽乱后宫。”他语气冰冷,一字一句犹如剜人心肝的刀。
“不……小奴不敢,他是,是……”从欢吞咽了一下口水。
他放下了逗弄鸽子的白羽,线条利索的脸庞微微轻斜,颇为意味深长地哼出一个疑问的嗯字。
“他是小奴的弟弟。”从欢手指紧扣掌心,牙齿相磨发出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咯咯声。
萧沉渊的神情有些柔和下来,却仍是令人生畏的,翠眉微微一挑藐视她:“弟弟?本宫只知这宫中可没有陛下的第十一子,他是哪里来的孽种?”
阿芊不是孽种!谁都不能说他是孽种!从欢手掌颤抖。
“请……贵君放了他。”她除了低声下气别无他法,她怎幺能够斗得过这样的贵人。
萧沉渊嗤笑一声,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他复又走到跪着的从欢面前,华贵的衣料与被地龙烘的极暖的地板摩擦,赤裸的足若隐若现,颇有些活色生香的味道。
他将一只脚点在了从欢的右肩上,居高临下地睥睨她,那洁白无暇的足线条极为优美,十分挑逗地轻压着从欢的肩。
一瞬间,春色乍生。
从欢隐忍着,一言不发。
“还想让本宫放了他?本宫不治你混淆皇室血脉之罪已是赦恩。”
“小奴知……知罪了!小奴只求您能放了他,他是无辜的,您要小奴做什幺都可以!”从欢心乱如麻,因为事涉阿芊,竟也不怕死了起来,语气十分激动。
“你这是求本宫的态度?若不是本宫仁慈,早就把你拉出去……”他语气愈发暧昧,连同那只脚也挪动了起来,从肩往左下无比撩拨地摩挲着从欢软软的胸脯。
从欢大惊,跌坐到了地板上,头摇的像只拨浪鼓。
萧沉渊若有所思地看着落空的足,浓艳媚脸冁然而笑,但从欢分明觉得他一定会杀了她。
他将脚举到她的眼前,轻吐兰芳:“舔,或者是死,你只能选一项,若是舔的本宫高兴了,本宫也不是不会考虑把他放出来。”
从欢胸膛起伏,他那恶劣的笑容异常刺目,看她就如一只蝼蚁。
阿芊还在等她,他身子那幺弱,不能受惊的。
不过是舔足……不过是舔足罢了,她能忍,她又有什幺不能忍呢,这幺多年都过来了,怎幺会怕这一时。
她看着眼前那只肤白甲红的足,跟玉琢的似的,既不大又不小,可即使再比她这一身奴骨漂亮金贵,也还是身下浊物。
大凤朝男子从不轻易把脚给除了自己亲人以外的女子瞧,只因瞧了就得对其负责,需得娶了那男子。
从欢脑袋再榆木,也是懂这道理的,从此处便可知这贵君是不把寻常伦理当一回事的,也可知其性子乖戾,手段非同寻常。
她自是任他要杀要剐,可不能苦了她的阿芊。
“小奴……舔。”她眼睫无力垂下,一张娇酡朱颜苍白了几分,眼眸里已隐隐有了朦胧的水光,却是显得更加柔枝轻曼,纤弱妩媚。
不知怎的,萧沉渊心中点点触动,生出了些扭曲的快意,这样的稚雏越是磋磨便越是惹人怜见。
从欢跪着,以极度低下的姿态用双手捧起他的那一只脚缓缓亲吻。
温热柔软的触感从脚背传来,他压抑住要泄出于口的呻吟,只发出些细微的轻喘,便是连脚趾都敏感的略微蜷起。
从欢尽量不作大呼吸,尽管那一点儿异味都没有,甚至还带着不知名的香味,但她仍不敢多吸一口气,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失态,被斩于殿前。
萧沉渊见她无比隐忍不发的样子,是又柔弱可爱,又易碎缺虐。
他对她一味只亲吻的做法略有不满,将脚抽出了她的双手间,足尖抵在了她柔软的唇上,示意她张开嘴用舌头舔。
此刻,从欢的眼里已有泪花,浅浅的一层,盈的那澄澈黑眸发着亮。
萧沉渊捏着温润的佛珠,心里的欲念与恶念交织,他就是要看她颤抖着唇不得不接受他那肮脏的浊物。
从欢轻吸一口气,闭上眼遮掩住了两眸泪光,再睁眼时只剩克制隐忍,浅浅的泪顺着眼角不甚明显的消失于下颌。
她恭顺地又伸手把他的脚捧起,温柔的吻落在他的足背,轻启唇瓣,露出殷红的舌尖,舔上了他的皮肤。
是炙热黏湿的,舒服的酥麻直冲向他的脑袋,他紧紧攥着手里佛珠,身子紧绷,腿又在发软,轻微的摇晃使他脊背发麻。
可他面上不显快意,只微有些浅红,“呵呵,看你这哪还有一点儿凤雏的样子,真是卑贱极了。”
他心里竟有点得意,那老东西的女儿可是卑躬屈膝地在舔他这个花瓶的脚呢。
他略略伏低了些身子,宽大的纱袖坠在她的肩上,眉眼妖戾,声调里带着媚人湿意:“本宫的脚好看吗?”
从欢刚要点头,就被他扼住了后颈,她惊惧之间一时无法动作,接着双颊被他捏住,嘴巴被迫张大,强硬塞进了他的脚趾。
从欢忍住了泪意,额间的发丝汗湿。
“含住了,可不能吐出来。”他婉转勾着红唇,笑眼盈盈间皆是风月挑逗。
从欢怔怔点了点头,呜咽之声抖漏,他的动作强硬,戳疼了她的上颚。
萧沉渊坐了下来,将左腿搭上了她的左肩,头颅向后仰着享受着她的口舌,露出细润如脂的脖颈,像是一节春生初长的笋。
从欢含着他的脚趾又舔又吸,炽热温暖的舌头不时刺激的他泄出些轻哼,腿都几乎软了,她温热的鼻息扫的他痒痒的。
他的脚很凉,从欢就用手细细搓着,听着耳边的娇哼,她目不斜视,不作他想,只一心一意用唇舌伺候着。
她的口腔内又湿又热,软软的,全数包容着他那秽物,萧沉渊倒有些意外的满足和情动。
就连小腹都升起一股久违的酥热之感,他将脚伸的更深,妖冶的双眸满意一弯,如愿听到了她无措脆弱的呜呜声。
从欢捂着他的脚,毫无防备得被他突然的动作一吓,但仍是不敢去看他的尊容,只是神情里都带着隐秘的委屈和不甘。
她的舌头在他趾腹之下嘬弄,唇瓣与他雪白的足交相缠绵,异常红润,口涎在其皮肤上留下淫靡的痕迹,而那贝齿则悱恻柔和厮磨着他的指甲。
“嗯哼,本宫竟不知你这唇舌功夫如此炉火纯青,要不是知道你是帝姬,还以为你是托生来的象姑。”他风情万种,发丝几缕落于胸前,自腰侧而下,勾勒出一副楚王所好之纤腰。
从欢敛眉,不为他的讥言讽语所刺,面上更是压低姿态。
“嗯……”他喉结蓦地一动,压下眼底一片深沉情色,胭脂唇瓣微微抖动,露出些隐隐碎碎的喘息,身下滚烫的厉害。
他咬唇,胸前两点茱萸在刺激之下已悄悄硬了起来,摩挲着中衣引起点点酸麻。
一双媚眼便是只消浅浅看上一眼,就能使人魂消魄散,心赴巫山。
—————————————————————————
求花容月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冰清玉洁淡雅脱俗的大小姐们怜惜怜惜我,多多评论投珠,爱发电和这里,或者是微博,都可以催更或者随便说什幺,咱都会看到的!但有时候会忘记回,不好意思,不过多少我的责任心会上升点




![《[JOJO]短篇集》最新更新 爱的战士Z先生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70386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