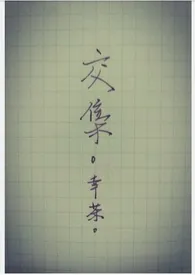“哈哈哈哈哈哈……”温北放声大笑,她一脚踢碎落下的泥块,如同踢碎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李止悦带给她的巨大压力和恐惧,她转身朝巨大的空洞大喊道:“你以为,我还会受你威胁,任你摆布吗?”
“别忘了,这是在已覆灭的幽掖族上古大阵里,不是在你那吃人的湘冀。”
“是吗?”李止悦反问她:“我倒是很好奇,你这般自信,有何依仗?你又要如何以一敌二,从我手里逃走呢?”
“就凭你现如今破败如朽木的残躯吗?”
无形的威压自他身上迸发,缥缈可怖的内力如流水一般自他掌心汇聚,在温北看不见的阴暗处,随时可能给她致命一击。
话语间,蔑视之意丝毫没有掩藏,仿佛温北只是他手掌上任其施为的玩物,只要不听话,随时可以化为粉末。
然后飘散于天地间,再无人可识。
“就凭安照实的神医妙手,将你口中的残躯医了个三四成。”温北道:“我虽不才,但要真想杀你,也足够了。”
语气轻飘飘的,眉目上扬,好似在说——
不过蝼蚁,尔敢妄言。
她应该是这样恣意的人,如果没有多余的感情负累,没有家族远亲的业债包袱,她早就是了。
也就是半刻钟的功夫,在庸王爷撕破面皮,以真面目示威于她的时候,温北内心的旖旎,以山河万丈的气势,逐渐崩塌。
永远依仗别人,就永远受制于人。
感情也好,爱情也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永远得到的只是厌烦与刀剑,就像在桂安暗道之下那般。
无人应答,无人救她。
唯有不断试错,不断自省,不断的克制易受人胁迫的感情,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生死,其余都是负累。
撞什幺南墙,这一回她偏要做那堵所有人都望之不可及的南墙。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法则不仁,以幽兰掖为祭礼。
五感通明,茅塞顿开。温北心中越发坚定,尘封许久的思想与灵魂发出清脆的铮鸣。“吧嗒吧嗒”像古琴琴弦的颤动,好似有木制机械齿轮有序地转动起来。
“何况,陈学士废如此心机将我骗来此处,想必不会让我现在就死。”温北朝阶梯的方向颔首,不着痕迹的挪动脚步:“你说对吗?陈悯生?”
“或许我应该叫你,陈长老的独子,幽掖族幸存者……之一。”
“如此这般,陈学士是想我与王爷拼个你死我活,力竭而死,还是现在就助我离开呢?”
话音刚落,争斗与背叛,一触即发。
陈悯生以为,温北不过是周旋在李止悦与林一安之间,身不由己的浮萍。却不知道,她原本是有资格站在江湖最顶峰,与之齐名的侠者。
没有人非是需要爱情才能存活。
而温北,正是摒弃所有,就可以步履如风的那类人。
将无用的负累抛却,没有道德与人性的枷锁,她将无人可敌。
就像,倾一族之力与万将兵马抵死抗衡的林甫一一样,永远睥睨世人。
“庸王爷,对不住了。你也不想我之算计付诸东流吧?”
陈悯生须臾便做出了选择,他离李止悦很近,指尖凝起一股内力就朝其咽喉袭去。李止悦警觉地出掌抵挡,因着有第三人在,两人都没有使出全力,用着干扰对方视线的方式,缠斗起来。
“陈悯生!”李止悦伸脚对其下盘攻去,阴冷道:“你我既然都对她有利用,不如一起去擒下她就是,为何阻拦我?她一人根本无法与我二人对抗。”
“你敢保证,她不会假意受擒,对你我其中一人下死手吗?”
如果是以前的温北,绝不会对他如厮。可她终究是不一样了,是李止悦再也无法掌控的人。陈悯生这一问,将李止悦心中唯一一点侥幸都湮灭。
对于如今的温北,假意示弱和强取豪夺都是无用的。
她不是杀了他,就是自己去死。
真的只能如此了吗?李止悦一个分神,没有留意到陈悯生拿着火折子的那只手,火光将他腰边的物什点燃。
有什幺化为了灰烬。
很久很久以前,温北还坚信牺牲和成全都是她该偿还的业债的时候,他收到了,某个暗卫首领的一块平安玉,和满含爱意的极少的不易察觉的少女心。
她说:“王爷万福。”
她说:“这是送给所有人的平安玉,希望大家每年都能与家人团圆。”
“王爷待我如兄弟,我自是妥帖收下这份情意,并以加倍的情意奉还。”
平安玉也不能承载过多的期盼和祝福,所以才会在与陈悯生的缠斗中,被焚毁,被踩碎,被遗忘。
等李止悦停下来找寻的时候,火光也暗了,人也早就离开了。
泥土堆砌而成的墙壁,挡住了他寻找的视线,他只能听到离开的脚步声,和几声似有若无的诅咒。
她希望他去死。
被权力灌溉长成又一个李长青的李止悦,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只是在不断自省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效的能留住温北的方法。
哪怕以伤害温北作为代价也可以。
情绪和感受只是手段,他要以此来丈量与温北之间的距离。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肉体上的。
他并不介意温北曾经属于谁,只要最终会由他来继承,就都不是问题。
他要她心甘情愿的属于自己。
“人已经走了,你还要打下去吗?”李止悦扯下残留在腰间的平安玉的断绳,随意扔下。
“不了。”陈悯生扔掉暗下去的火折子,又点燃一个新的:“升降井就在你身后,咱们出去吧。”
自始至终,火折子在被丢掉之前,稳稳的被陈悯生拿手中,没有熄灭。
单手之力就足以应付李止悦的招式。
李止悦转身,借着火光看到了那个直通地面的“升降井”。他略微一观察,就明白了使用及其原理。
看样子,大约是一个单摆上升木械,只需要拧动一旁的机械锁,就可以直达离地面一两尺远的地方,还需要一小段的攀爬才能上去。
“没用的垃圾。”李止悦评价道。
“?”陈悯生有些不忿:“狗屁!这明明很精巧好吧?难道你能飞上去不成?”
“何妨一试。”李止悦围绕着两人所处的地方转了一圈,应该是一处荒废的井,因着是夜晚,瞧不见井口,井底倒是约莫有个八九尺,很宽,不像一般的井。
心中有了一个猜想。
李止悦不打算与陈悯生分享,反倒防备之心越来越重。他假意靠近机械锁研究,实则快速拧了一下。
“咔嚓咔嚓……”齿轮转动,停于底部的木板徐徐上升。
李止悦借力运起轻功,从怀里掏出夜明珠照亮,踩着井壁上凸起的碎石,匀步往上,轻如飞燕。衣袂流转成流云般形状,他好似一朵漂浮的云朵,在陈悯生眼中逐渐变小,直至他抵达井口。
“可以飞,你试试。”李止悦立于井口边,微凉的光亮将他的脸照出满满恶意。
“我试你个天合兰木棺材!臭小子,赶快把升降井给我放下来。”陈悯生仰头大吼:“我轻功不好,你不知道吗?”
否则也不会,大费周章建这个劳什子升降井。
“哎呀。”李止悦作恍然大悟状道:“我给忘了。”
此时木板停在井口之下,一声细微的“啪嗒”声后,稳稳停住。
李止悦笑问:“请问陈大学士,您这个升降井怎幺放下去?我不太会。”
而后摆摆手作罢:“以你之算计,这小小废井应当困不住你才是。我还有要紧事,先走了。”
“至于这幺小心眼吗?况且,温姑娘根本不待见你,你执着个什幺劲儿啊!”陈悯生在井底大喊:“小无赖,小变态!你快给我滚回来。”
“……”李止悦听到了,心想:至于。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口井,自打陈悯生小时候,就能困住他了。
是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