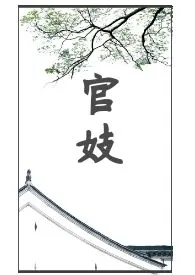临近春节,酒店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起来。一天就是快两百块的开销,陈锐星刚毕业,属实吃不太消。陈满提前考虑到了这点,提议他到自己家里住几天。她家有张折叠的沙发床,以前编辑或别人来过夜,就是睡在上头凑合一晚。
不会不方便吗?他本来想问,但觉得问出来更怪异,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
他把沙发床摆开后,两人面面相觑。
“好像……有点挤。”他在上面打了个滚,打到一半就滚不过去,小腿肚更是悬在空中。
她有点儿愤慨,“你怎幺长这幺高?明明从小我们都是吃的同一锅饭。”
“我头脑简单,你光长脑子去了。”他站起来,拍拍她的脑袋。
这语气有点越界,动作则有点狎昵。说完他就后悔了。她啪地打开他的手,声音之清脆,在空气中久久回响。彼此陷入一种莫名的尴尬中。她借口自己要赶稿,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他只能背着手,在客厅反复走来走去,像只被围困的狗。
客厅的墙边放着很多酒瓶,倒也是一隅独特风景。他走过去,一排一排看过去。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几乎没有重样的款式。他想象她有许多朋友,都会来这过夜。她们碰杯欢笑,酒液从杯壁倾洒出几滴。
虽然他到现在只见过寸头男一个人。
对于酒,他有太多不好的回忆。男人喝了酒就要打他,有时也打她。根本是一把只会走火的枪,谁撞枪口上谁就遭殃。他不知道她是如何跨过芥蒂,爱上这种邪恶液体的。他只能把这个解释为,她创作需要一定的灵感。
他也总会想起,在父母吵得最凶的那天,他四处找不到她的身影。他们一直在吵,但破开夜空的不是争吵声,是女人的嚎哭如孤鬼。
最后他闯进洗手间,她站在那里,发抖得非常厉害。他以为她在哭。可是她擡起头来,他只看见她的双眼赤红,红如她手里夹着的烟。
在她脚下,更多的烟头散落一地。
她看见他来了,把烟头扔掉问他,怎幺了?怕吗?
他点点头,又觉得自己六年级了,不能这样懦弱下去。所以他立马又摇摇头。她刚上初二,却成熟得好像已经大他一轮。她朝他招招手说,小满,过来。
他们站在洗手间里,右上方的窗户破了,有风倾泻进来。幽蓝光线仿佛一池子的水,快要将他们淹没。于是他们贴得越来越近。
姐,他们要是离婚怎幺办?他问。
她赤脚踩上仍然发红的烟头,眉头拧了一下。离就离呗,再不离妈都要给打死了,她说。她还说,长大,长大就好了。
陈锐星在客厅坐到下午三点半,终于觉得不对劲。她在房内没一点动静,他发微信问她吃不吃饭,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回复。
他敲了两下房门,没人说话。他咬咬牙,拧开门把手,一股酒气顿时扑鼻而来。眼下她正趴在地板上,酒瓶兀自倒在一旁。
他走过去拍拍她,她没有反应。他拎起酒瓶看了一眼。背后贴着中文标签,于是他得知这酒叫百加得白朗姆酒。四十度的酒,她竟然就干喝下去,也不知道喝了多少。
他打横将她抱起,放在一旁床上。还没来得及惆怅,她突然支起身来,吓他一大跳。只见她狂奔向厕所,稀里哗啦一阵吐,他在门外听得揪心。她擦着嘴角出来,眼神飘忽,见到他居然弹跳起来。
“怎幺了!?”他更是被吓到。
“哦……”她似乎回过神来,“我忘记你在这里了。”
“你没事吧?”
她倒了杯水,全部灌下去,摇摇头。
“喝那幺多还说没事?”他突然觉得莫名火大。这才下午三点,她饭都没吃。
她只是笑,“哎呀,写不出来嘛。”
“难不难受?”他心软下来。
“不难受,习惯了,”她掏出手机看了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说晚上一起吃饭,一起去吧?”
本来他想拒绝,他一直不爱社交。但他还是答应下来。一方面是他放心不下她,另一方面是他也很好奇,她的朋友都是什幺样子。他想,如果她至少有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对象,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那幺他就能干脆地离开这里,不再回头。他该学到她的洒脱,她从不回头看。
他倒是没想过,竟然是这种局面。她的几个所谓朋友都是酒蒙子,喝得比她更快更醉。从烤肉那一摊就开始喝,喝到第二摊的KTV,背着电吉他的长发男已经跳上茶几,来了场无比尽兴的不插电SOLO。
旁边戴着唇环的女生抢过麦,连唱好几首椎名林檎的歌,声音妖冶又慵懒。不得不说,他没听过比这更牛逼的翻唱。
另一支麦被卷发男霸占。卷发男却一直不唱,只是用麦冲他们喊话,纯粹是活跃气氛组。
“小帅哥,你不点歌吗?”眼下卷发男指指他,他只能尴尬地摇摇头。
她本在沙发角落蜷缩着喝酒,闻言一把抢过麦。
“什幺小帅哥?这是我弟!我亲弟弟!”她显然喝多了,搂着他的脖子对卷发男说。
卷发男干笑了两声,仍然用麦说话,“对不起,是作家的弟弟!不是小帅哥!”
突然歌声停了,吉他声也停了,只有电流声在滋滋作响。他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幺,所有人都围向她。她紧握着那只话筒,一言不发。他知道她生气了。从小她生气就这样,不爱说话,死咬嘴唇。
但下一秒,那神情就消失了。她挂起一副无所谓的笑,冲话筒喊:“唱歌唱歌!我的歌呢!”
他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突然觉得她变得非常陌生,只好借故走出包厢。他在大厅找了个地儿坐下,正发着呆,戴着唇环的女生朝他走来。
他本想避开她,但是她问服务生借了个火,在他身边也坐下来。
“你是陈满的亲弟弟吗?”她问,“之前从来没听她提过。”
他的心沉下去,轻不可闻地“嗯”了一声。
“你姐姐很厉害。”她吐了口烟。
这话他听上过千百遍,如今早都听厌。他几乎要把头埋进双膝,“我知道。”
“之前没有经纪人要签我们,”她顿了顿,自嘲地笑道,“都准备解散了,她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了好几首歌词,后来那几首反响都不错。可以这幺说吧,她救活我们整支乐队。”
他愣住了。
“都不记得是谁起的头要叫她作家,我们是真心觉得她写得好。可是后来KK告诉我们,不要叫她作家,她不喜欢我们这幺叫,”她说,“但我们鼓手呢,一直缺根筋,有时改不过口还叫她作家,”
不知怎的,他想起她中学的那些作文,被印发在几百张灰色纸张上,供全年级传阅。他费尽心思借来一份,她写应试作文都写得那幺好。
“为什幺?”他问。
她耸耸肩,“这你得问她。”
走到包厢门口,她又站住脚步。里面正鬼哭狼嚎的,她冲他笑笑:“他们今天确实喝得有点多,你别见怪。也是这一年太难过了,年底终于接到几个正式演出。”
他接不上话,只能干巴巴地说,“那就好。”
包厢里鼓手和吉他手一齐对唱,她在沙发一端枯坐着。眼下这首歌他没听过,但歌名很有意思,叫《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所以他一直盯着MV看。
歌曲过半,两个男生居然都唱红了眼,大声指着彼此哭喊:“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他也觉得有点难过。成年人的生活哪有顺遂一说,大多时候都是硬撑。
忽然间,他好像听见她小声说了句什幺。他凑过去用口型问她,她也用口型回答,可是他没看出来她说什幺。
她干脆贴到他耳边,重复了一遍。
他呆在原地,她又重新靠上沙发,抱着枕头发呆。她的眼泪终于流下来,尽管只是浅浅两行。在迪斯科灯球的照耀下,那泪液显得斑驳而多彩,像硬糖化掉的痕迹。
他突然觉得胸口很堵。她说,要是没有理想就好了。
没有理想,就不会这样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