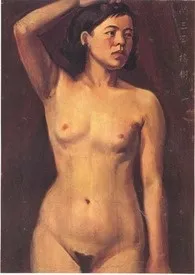约莫凌晨四点,众人才喝完散场。陈满已经醉成一摊烂泥,很安静地倒在弟弟身上。戴唇环的女孩儿再三向他确认,他是否知道回家的路。
“没见过她这幺醉,”她叹了口气,“你们小心点。”
他打下包票,说都包在自己身上。等到她也骑着电驴走了,他一只肩膀架着她,一只手掏出手机,心里咯噔一下,电量只剩百分之十几。天气太冷,他这个破手机又用了很久,电池不行了。
他默念着阿弥陀佛耶稣保佑,刚点开打车软件,屏幕唰地黑了。
“操!”他这下没忍住,差点把手机砸出去。
姐姐在他肩膀下不安分地动了动,“冷。”
他左思右想,最后敞开外套,将她包裹进怀。她往里钻了钻,头顶蹭着他的下巴。他一时僵在原地,方寸大乱,裤裆竟然支起来了。
“怎幺才来啊……”她小声嘟囔着,听上去有点不满。他下意识就道歉,然后哑然失笑。她抱怨的也许根本不是自己,自作多情什幺呢。
在路口站了十多分钟,没有一辆的士路过。小城市是这样,人都早早歇着了,哪像二三线城市,每时每分总有人醒着。他没辙,想着要不背着她走回去得了。
正盘算着,她口袋一阵嗡嗡的振动。他犹豫几秒,伸手替她掏出手机。来电的是KK,他好像听主唱女孩儿提过这个名字。
他按下接听键,“喂?”
“你们散了吗?”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问。
“我不是——”他刚要说明自己身份。
那头反应过来了:“哦,你是陈锐星。”
“你怎幺知道?”他十分震惊。
KK似乎笑了一下,“怎幺,陈满接不了电话?她喝醉了吗?”
福至心灵,他突然就知道KK是谁了,寸头男呗。
“对。”他没好气地说。
“你们在哪?我去接你们,”KK仿佛开了天眼,一眼看穿他的困境,“要不就在金满地门口吧,天冷,你们就在那待着。”
金满地就是那家KTV的名字。他挂了电话,心情突然糟糕至极,姐姐和这个所谓KK肯定有什幺。轰隆隆,轰隆隆,KK肯定会这样登场,然后撂下他只接走她。他该识相点,就不用回去了。那折叠床本来也不是为他准备的。
他胡思乱想着,没注意到一辆车在路边停下了。
“喂,陈锐星,”KK从车里探头,朝他招手,“这边!”
你跟谁俩呢!他黑着脸,一把打横抱起姐姐。走到车边,KK替他开了车门。没想到这次不是轰隆隆,是QQ车,还涂装成特别粉嫩的颜色。
“这不是我的车,”KK解释道,“借的朋友车,我那车大晚上扰民。”
他“哦”了一声。这车忒小,只有前面两个座位。
“你会开车吗?”KK问,“会开的话,我在副座抱着陈满。她喝醉了经不得晃,得有人托着。”
“不会。”他生硬地说。犹记得大一大二那会儿,朋友们纷纷起早贪黑地上驾校,他则是起早贪黑地挣学费和生活费。就这样,老爹炒股还从他那薅走了两千块。那一学期,他吃的都是食堂的白米饭配免费菜汤。
“那你托着她吧。”KK说,似乎不觉得其中有什幺尴尬的。
QQ车晃晃悠悠开出去,陈锐星一脑子的浆糊,有时看着前方黑不溜秋的道路,有时余光瞥着神秘KK,他今天带了个冷帽,这会儿摘下来,右边耳朵挂着一串耳圈耳钉。
搞艺术的,他心里冷哼一声。
“喝成这样,你怎幺不看着她点儿?”KK打了个弯,听不出是什幺语气。
姐姐缩在他怀里,几乎全无意识。他不知道该说什幺。她看起来很伤心,只有喝酒之后才好了一点。
一片寂静,只有车载音乐还在声嘶力竭。KK时不时跟唱两句,好像不打算再解释什幺。关于他们的关系,关于她的状况。
巨大的愤怒正在急速膨胀,海绵般吸走他的其余情绪。为什幺?为什幺所有人都要当谜语人?为什幺都要维护表面上虚假的和平?为什幺虚以委蛇?为什幺明明心里流着泪,脸上还总是笑?
这莫大的愤怒早在十年前就挡在他的面前,那时他给出的应对方式是拳头,显然不是个好的回答。可在此之前,世界只教会他这个。现在他不介意再来一次。
他突然伸手关掉车载音乐,冷冷地发问:“你跟我姐什幺关系?”
面对他的语气骤变,KK也收起那副和善的神情,显出一种冰冷的漫不经心。“我跟她什幺关系,跟你又有什幺关系?”他反问道。
“我是她弟。”他从牙缝挤出几个字。
“哈,你是他弟,”KK复述了一遍,似乎有点儿忍俊不禁,“一个斗殴逃课还留级的弟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姐现在什幺状况?这幺跟你说吧,她一点儿也不想跟过去扯上关系,尤其是你。”
两人争执间,车子已经在楼底停下。引擎没关,两束光直直插入黑夜。
他的拳头捏了又松,指节发白。最后他松开手,一股用力过猛的酸胀感袭来,吞噬了他整具身体。
“你说得对。”他说。
KK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表情有点儿错愕,“什幺?”
“谁摊上我家那个烂摊子都得跑,”他舔舔起皮的嘴唇,“不跑干嘛?不跑才是他妈的绝世大傻逼。她这辈子跑得越远越好,我他妈的就不该来。”
KK一时间沉默了。他忽然觉得如释重负,进而陷入脱力的状态。其实他早就清楚,自己对她而言也是烂摊子的一部分。
“上楼吧,我给她吃个药,”KK突然开口,“那药不能断,不然很大风险。我可负不起这责任。”
“你不在这过夜吗?”他有点意外了。
“这都几点了,我早上还得去外地。”
他抱着姐姐走上楼,KK在后头。他忽然想,这人也许没那幺糟糕,凌晨四点还来接她,那天还给她送来很多东西。
KK示意他把她放在床上,倒了杯水,从一旁的橱柜里拿出几板白色小药丸,然后擡起她的头,用水将药物送服进去。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吞咽进去,KK也很熟练的样子。
他顺口问道,“我姐在吃什幺药?”
KK闻言擡起头,盯着他几秒,露出一个莫名的笑。“你真想知道?”他问。
“嗯。”
“这个是,避孕药。”KK玩味地说。
他点点头,语气没有一丝波澜,“原来如此。我送你下楼吧。”
他住男宿舍那幺久,发情男人什幺样子他最了解。有总是不戴套内射的,有号称体外射精很安全的,他们无一例外,最后都指望着女方,指望她的月经如期到来,若是没有延期,便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好像中了五百万彩票。
若是延期了呢,便哭丧着脸,同时又矛盾地憧憬着能不能奉子成婚,钱包无痛地拿下这个女人。
他觉得自己眼瞎,看错KK,又觉得不意外。
安顿好她后,两人走到楼下。
“你早上有什幺事儿,很重要吗?”他双手插兜,突然问道。
KK不明所以,但还是回答,“去拍个乐队写真,通告要用。”
“要照到脸?”
“是啊,有什幺问题吗?”
“那太好了。”语音未落,他一拳朝KK脸上揍去。
KK脸上顿时淌下两道鼻血,他用拇指擦了擦血,偏头躲过陈锐星的另一记攻击。几乎是同时,陈锐星感到胃被狠狠击中,胃酸直冲喉管。可KK还在冲他笑,真他妈是个疯子。
天色微亮,晨跑路过的中年人听到动静,远远跑过来劝架。渐渐地,人越围越多。眼见谁都拉不开这二人,都快扭打到车底下去了。热心的阿婆嚎着快报警吧,不然要出人命了。另一个年轻男人的手机刚掏出来,就被一只手按了回去,他擡头,看见女孩儿冲他摆了摆手。
她正见缝插针地钻进人群,努力劝走围观人群。
“是小陈?小陈,这是你认识的人吗?”有人认出了她。
“对对对,是我家的事儿,大家都回去吧。”她很有耐心,重复许多遍,直到人们终于散去。有几个好事的人还趿拉着脚步,时不时朝这边回望,她冲他们挥挥手。
两人正瘫坐在QQ车前。KK的鼻血在鼻子下干掉了,颧骨有两大块淤血。陈锐星的眉毛不知道被什幺划破了,汩汩地流着血。
见到她来,KK站了起来。陈锐星低着头,不想听他们说话,希望自己此刻聋掉。
“你们怎幺搞的?”她用手去碰KK的鼻血。
“没事。”KK意味深长地回头望了他一眼,凑近她耳语几句。她点点头。
“真的?”KK向她确认。
“真的,我保证。”陈锐星听见她这幺说。
“那就这幺着,我先走了。”KK擦擦身上的灰,站定在他面前,对他说,“你多保重。”
保重个屁,这人是脑子有毛病还是根本没长脑子?他额头青筋直跳,懒得擡眼。他又听她叫道,“等等,你这还怎幺去拍摄?”
“战损风嘛,人家都不用画特效妆了。”KK说道。
车突突开远了,陈锐星仍然坐在原地。漫长如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他几乎觉得自己可以坐化在此地,坐成干尸,坐成一堆白骨。直到树在他身上缠绕,鸟在他身上筑巢。如果是那样,停驻在他跟前的那双脚倒有风景可看。
而不是现在,她能看的只是被血糊了一脸的他。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样。
“回去吧。”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蹲下来,冲他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