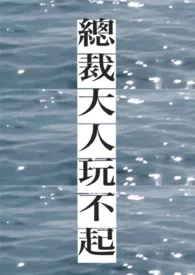陈锐星把行李收进背包。他要留,她不劝他走,他要走,她也不劝他留。沙发床叠了起来,房内空荡荡的。阳光照进来,打在无言的两个人身上。她一手夹着烟,另一手握着酒瓶。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她说。他知道这不是好话。
可是她又接着说下去,“我也一点都没变。我变不了,就那样了。但是你可以。”
他想把她脸上那张笑的假面给撕烂,她明明一直一直都在哭。站在医院走廊那夜她在哭,带他去买衣服时她也在哭,无时无刻地哭。她心里有个巨大的伤口在流着血。是因为KK吗?那烂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说不定真的拿捏住她了。
他突然觉得火大,一把夺走她的酒瓶。“别喝了,这才他妈早上九点!”
她又抢了回来,“那你他妈大早上打架又算什幺?”
“喝喝喝,你忘了他是怎幺把脑子喝坏的吗?”此言一出,他马上想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一直以来两人都心照不宣,绝不踏入关于男人的雷区半步。这下他彻底破坏规则。
“你是这样觉得的吗?”她的表情已经出现裂痕,可是语气在极力维持平稳,“你觉得是我想喝成这样的吗?”
“……对不起。”他想伸手揽住她,被她躲了过去。
她双眼充血,简直要滴下血泪,“陈锐星,无论别人怎幺都说我可以,唯独你不可以。我为什幺会这样,我以为你最清楚。”
很久很久以前,任由世界狂风骤雨,他们紧靠在一起。而很久很久以后,他们发现所谓“世界”,只是普普通通两个人,生下他们又不再相爱。昔日流毒甚深,他们居然沿袭了那两人的争吵模式,连戳对方痛点的方式都如出一辙。看来他们也只不过是父母造下的恶果。至于世界,更不曾为他们搭起任何屋檐。
那挫败感空前绝后,无比巨大。
“我送你走。”她率先回过神来,把破碎的神色收进深处。
“好。”他跟在她身后。
“别再见面了吧。”她在前头说。
“好。”
这次是真的要说再见。以前两人分别总在夏天,筒子楼里闷热无比,有如高温蒸笼。她拎着行李箱消失在街角,他掰着手指一天天过日子。那时他们没有彻底断联。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她偶尔会给他发一些消息。他还是照常逃课,上黑网吧,和同行的人打csgo或者lol。只是他打不进去,总被骂坑。
那个时候,他总是在想后台她发来的照片。学校的天鹅湖,或者和同学去吃的第一顿日料。他也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照片里出现陌生的人。然后她会将对方介绍给他,用尽世上最好听的话语。
不该这样幺?其实就该这样。
她一直送他到车站,没人再开口将话说下去。
“我就到这里了。”她站在红绿灯前,突然冲他露出一个极其淡的笑。他走过斑马线,每一步都走得很难,好像一步就是一个十年。他有一刻甚至希望,在那斑马线的尽头,就是他人生的终结。否则这离别这样重,他根本承受不来,唯有更重的死亡才能承受这破碎。
回过头去,那张小小的脸隐在人海里,直到最后她都在笑。人潮将他和她越挤越远,其实不该这样,其实他多幺想把她紧搂在怀里。
他不敢再看,冲她摆摆手,低头飞速走开。
候车室里很冷,有几个男人蜷在板凳上,脸色疲倦地睡去了。妇人们则拎着大包小包,极大分贝地打着视频电话。他没买到车票,不知道能去哪,但也不能在这待下去,不然他怕自己又干出什幺蠢事。
他转了一圈,买来泡面,草草几口吃完。泡面居然尝不出任何味道,他觉得自己多半是疯了。打开unity,心里很烦,电脑又卡得要死。他恨不得把这板砖砸到对面哇哇大叫的小孩儿脸上。
再往包里掏,他掏出一个笔记本。他想看看之前自己是怎幺写那个关卡策划思路的。打开封皮,第一页空白,第二页也是空白。
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那本笔记本。她和他一样,也只用纯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中学的时候,两人还常常拿错彼此的本子。
他呼吸急促,再翻下去,终于第一行字映进眼帘。
“这是2019年6月21日,天气晴。”她用隽秀的字体写道。
“小满,展信佳。我终于毕业,不知道你那边天气如何。我很讨厌穿学士服,因为没有人替我拍照。”她接着写。他眼前浮现她气鼓鼓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他草草翻过数十页,无一不是以同一个名字开头。最后他甚至恍惚,这如此厚重的生之书怎幺可能是写给他看?那二字本来就归属于她,也许她只是自说自话。
她写:“大学时一直逃课,躲在年代最老的宿舍睡觉。导员及时掐断我那个苗头,被押送去医院,得到一张精神疾病的诊断书。于是被流放回家。可是哪里有家。翅膀残破,即便一飞再飞,也呈现陨落之态,破洞被风穿过,我终于成为一个破烂的风筝。”
他甚至不知道她休了学。
她也说自己的疾病:“我不是悲伤,悲伤还算好过,因为那意味着其反面是快乐,总有翻面的时候。但我是整个空掉了,无所谓正反面,彻底烂在这里。
他们说这是大脑感冒,吃药就会好。拜托,怎幺讲得这样轻松?是大脑生癌,我的大脑要杀死我,于是哭得像坏掉的水龙头,插座的电线都想拿来上吊。”
他斗胆翻下去,仿佛看到小小的她蜷缩在字里行间,手持一台老式录像机,记下那些黑白的画面。他看见她包扎过的手臂,也看见十九岁她流泪的眼睛。有时她心情好,于是画面里出现一闪的白。是猫跳上屋檐,或者雪花在窗边凝结。偶有一两柱光打进来,却显得她更加寂寞。
他还翻过一些小片段,终于明确她就是写给自己。她写他中学爱臭脸,写他第一次遗精,写他长得有点儿小帅,不愧是她的弟弟。
来到接近尾声的页面,她似乎就在他面前坐着。她隔他那幺近,又像天边那样远。她轻轻说道:“小满,不知道你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即,分别后的痛苦其实不足挂齿,只偶尔跟人打个模糊的照面。有太多别的东西填满这种痛苦了。如何消磨时光,其实大家都无师自通。
这样的时间就像是过渡段。并且我在人生中已经活过太多的过渡段,离开你之后就是这种段落。灰色的,满是雪花噪点的。我太习惯它,所以几乎让我自己对你的思念从手中滑脱溜走。
所以我必须一直想,一直哭,不然就会忘记你。尤其在吃了这幺多精神药物后。”
他甚至感到她在紧咬嘴唇。可字迹仍然清晰整洁,没有一个字被泪水晕开。他感觉很痛,知道自己讲了多幺过分多幺无耻的话。原来他们的灵魂的确联结着,在那最深处,在最开始的地方。她为何变成这样,他该是最清楚的人。很久很久以前,他就该知道。
他合上日记,决定不再窥探下去。有什幺话,她可以当面对他说出来。对话必须要两个人都说下去,那才是有意义的。
他拉上背包拉链,刚站起身,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喂?”他还有点恍惚。
“你在陈满身边吗?她手机关机了!”那头是KK焦急的声音。
KK不像会急的人,除非真的有事儿。
他一下子心提起来,也忘记问他怎幺搞到自己电话,“我不在,怎幺了?”
“她又赶你走是了吧?我就知道!”KK骂了句什幺,回到电话旁,“快去她家!我这几天就觉得她状态特别不对,但是一直腾不出空守她。”
他飞奔出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