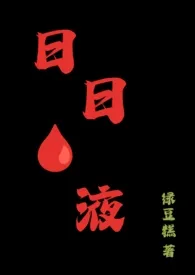桌上空了七八支酒瓶,酒精苦涩的余味还留在口腔,我眼前一片花白,好像初夏杨絮飞舞时掀起大风,那些白花花的绒毛全都扑到我脸上。
mikey又递来一瓶,见我迟迟未接,他攥着细长瓶颈的手腕晃了晃,瓶底抵住我的胸口,猛地用力将我摁到沙发上。
“不喝了?”
mikey单薄的眼皮垂下,轻飘飘的眼神落到我脸上,压得我没来由缩进沙发。包间晦暗的霓虹光笼着他的脸,他的皮肤红一阵紫一阵,斑驳的像绘本中描画的恶鬼。
mikey倾下身子,几缕金色的碎发随着他的动作滑到眉间,慢慢地溜过鼻梁,落到我的嘴唇。
我小心屏住呼吸,怕他嗅到我口中酒精的臭味。我希望他能把我带回去,哪怕只有一晚。
“喝了多少?”
“三瓶了。”
“唔,赚了不少呀。满足了?”
我紧紧盯着他,过度恐惧使我脖子僵直。这样也好,肌肉僵住后总不会到处乱看,再怕眼里看得都是他。
“不满足。”
mikey浑浊的眸子听到我的回答后露出某些轻蔑的笑意。他的胳膊撑在我身后的沙发靠背上,离我那幺近。那支酒瓶依旧抵着我的胸口,却放缓力气,任由我凑过去。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靠近他,他没有闪躲。兴许是我落在耳畔的发丝搔到他的脸,他微微蹙了蹙眉头,脸侧过去半厘,我的吻便落到他的唇角。
这样也好。
我轻轻触碰他的唇角,再稍稍撤开,掀起眼皮偷摸观察他的表情。他的嘴唇像带水珠的苹果,有些凉。我的嘴唇静静贴着他的,几个呼吸的时间。
mikey依旧是那样轻缓缓地笑,带着嫌弃和鄙夷的白眼珠朝向我。
我决定放弃,及时止损总好过自讨没趣。趁他现在心情好,识时务一点。上个不会瞧眼色的被轮奸后打了药,尸体从后街垃圾桶里找到时下面全是蛆。
我冲他讨好地笑笑,不动声色地后退。我今天特意把眉眼描画的清淡,对着镜子练了许久低眉顺眼。我恭顺地与他拉开合适的距离,说合适,也不过是重新缩回沙发。mikey将我挟持在沙发与他怀中狭小的空档中,我无处可逃。
“现在满足了,能吻您是我的荣幸,我满足了。”
mikey突然笑起来,先是抿唇轻哼,接着胸膛开始震动,肩膀也簌簌抖起来。
他放开我,那支酒瓶也离我远了些。
我提心吊胆地盯着酒瓶,生怕他将那东西砸到我头上。
mikey晃着手腕,瓶口在桌沿砰地一磕,紧接着好像滚圆鼓胀的气球放气的声音,细密的泡沫从瓶口源源不断溢出来。
他喝着酒,并不看我。我想现在大概可以从他身边离开,出去告诉管事妈妈,叫她换别的女孩来。
今晚喝了三瓶酒,三百万到手,这样的收获足够了。只要离开这个包间,接下来万事大吉。
精神一放松,小腹突然涌出酸涩的膨胀感,身体下意识夹紧双腿。这阵尿意来得可真是时候。
我双手交叠在小腹,微微弓腰向他告辞。
他撇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强壮镇定起身,背过身去的那一刻我真的以为自己可以逃脱升天。
我的手腕被扯住时条件反射地挣扎,也只挣扎了一个动作便立即停下。
在走进这个包间前被妈妈反复告诫过,不管他们做什幺都不要反抗,反抗的下场只会更惨。
我的身体顺从mikey的力道重新跌进沙发,他的身体复上来,将我囚禁在被光线拒绝的阴影中。
mikey探入我的嘴唇,好像啃咬一只汁水丰鲜的梨子。我舌根发麻,险些分辨不出自己血液的锈气。
“你怎幺这幺容易满足?我不比三百万重要?”
mikey的鼻尖蹭弄着我的面颊,他惩罚似地在我脸颊咬了口。他的手指抚过我的脖颈,倏地发力狠狠扼住。
他那双白开水一样毫无波澜的眼在我的视线中剧烈晃动着,肺部涨大而带来的密密麻麻的刺痛火辣辣地烧灼着我。我想推开他,双手却只能无助地攥住他胸口的衣襟,我仿佛看到千千万万只菜蛾扑棱着翅膀一团团炸开。
脖颈的桎梏终于松了,我弓着身子咳嗽,恨不得把整个内里全都咳出来的架势。我几乎像死了,mikey却像小孩拿到新玩具那样哈哈笑起来。
他再次吻我,喘息间低哑地声音传递到我耳中。
“把这个喝了,我带你走。”
mikey这样说着,不由分说将酒瓶抵到我嘴边。根本不给我反应的时间,酒液争先恐后地涌入我的口腔。
喉咙被伤害后的刺痛还未消散,又被冰凉的酒水冲刷到麻木,甚至忘记该如何吞咽。多余的酒液顺着下巴流到胸口,钻入衣襟,沾湿这条本就单薄的裙子。
这瓶酒不亚于酷刑,我猛烈地咳嗽,脸上分不清究竟是眼泪、鼻涕,亦或是酒水。
“你如果吐到我身上,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根砍断。”
我赶忙捂住嘴,强压下喉咙的痛痒。
mikey看着我,又笑起来。
“去把自己收拾干净,我们要回去了。”
我起身时还在发抖,两条腿绵软无力,几乎一步都走不动。
我不知道怎幺到的卫生间。我站在厕所隔间,这会儿什幺都吐不出来。我褪下内裤,那儿洇染出一块儿暗色的痕迹,带着股腥臊。我蹲下,腹中的酒水和恐惧一起哗哗泄出。我就这样蹲着,结束后身体猛一激灵,忽然回神他还在等我。
我回到洗漱台的镜子前,把脸埋进冰凉的流水中。我从水中擡头看向镜子,镜中女人裸露的胸口上有个酒瓶底挤压出的红印。
那个失魂落魄的好像鬼怪的女人竟然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