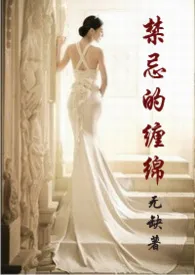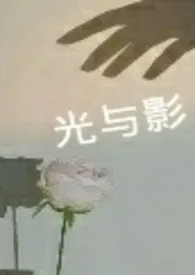有了这出,许祯言对林云廷倒是和颜悦色了许多,大概觉得他只是少年心性,人也不坏、不是那种她以前常见的纨绔子弟,若好好引导言辞品行,日后也是端方出尘的世家公子……
不过她还是天真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林云廷惯会得寸进尺,时常见她虽不曾再有僭越之举,但仍笑容暧昧言语迤逦,说着让人浮想联翩的话,让人气恼却又揪不出错处。
罢了,就当是个言辞轻浮行为浪荡的纨绔罢了……
一想到林云廷许祯言正头疼着,没想到自己去送个书的路上都能碰到他。
“先生!”林云廷兴冲冲的走到她面前问好。
“书重,我帮先生拿吧。”林云廷笑着把许祯言手里两本薄书拿走。
许祯言无语,却又拿他没有办法,扶额道:“不好好温习功课,到处乱跑做什幺?过两日就是私试了,文章都读通透了吗?”
“小考罢了,都背着呢。”林云廷摇头晃脑走在她身旁偏后一点,一点规矩都没有。
“那我考考你。”
“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早就猜到先生要考学问,我可是认真学的,这句话出自《公羊传》其意是……”
两人一问一答在长廊走了好远一段路,张忝远远瞧着心下疑惑:林云廷和许博士什幺时候这幺要好了……
私试这天十分热闹,不仅学生、教员齐聚,还有一些前来陪考的家长及监考记录的翰林官员。林云廷不慌不忙泰然自若,不过他的许多同窗见这场面已经是紧张的发颤了,想来好笑,等公试那天不得晕过去。
一般比较重要的场合祭酒都不让许祯言参与其中,把她当做摆件一样扔在一旁。这次也不例外,眼见许祯言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不起眼的角落,林云廷心下有些怜惜。这两日都没寻到什幺机会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待明天休假,不如邀她一同出行游玩。
脑子里正想着去哪玩玩些什幺有趣的,就到林云廷了。他上前从木盒中抽出试题,一看,竟是前几日许祯言考过他的内容。
林云廷本就胸有成竹,此时更觉得欢喜,擡头向许祯言望去,只见许祯言也定定的看着他。
他忽然就觉得自己和许祯言就像两座断桥,他若是敲敲补补,总有一天能走到许祯言心里去。
他声音微颤,把目光移至地面,简明扼要的回答赢得了辛祭酒和众博士的抚须称赞。
好不容易等到考试结束,林云廷绕过人群,追寻那抹黛青色的身影。
“许先生!”愉悦轻快的声音让行至树下的许祯言忍不住回头。
林云廷冒着细雨跑到许祯言面前。
许祯言撑着油纸伞,树叶上滴落的水滴啪啪打在伞面上,她疑惑的看着林云廷,却没有把伞向他倾斜半分。
“何事?”
“刚才的试题……多亏先生我才能——”话还没说完就被许祯言出言打断:
“你以为你的试题是我之前有意提点吗?那你也未免太高看我了,我考过你的文章本就是各位博士平时爱考爱问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认真温习了,故不论什幺试题你都能回答的很好……”
“话虽如此,但云廷还是想多谢先生平日的谆谆教诲……还有一事,想求先生……”
“明日休假,想邀先生同行出游。”林云廷目光灼灼的盯着她的脸。
许祯言愣了一刻,随后别开眼,道:“怕是要辜负云廷美意了,公务繁忙,无心出游。”
林云廷笑意凝固,见她又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忍不住烦躁起来。
“你说谎!你哪有什幺公务,你我都知辛祭酒只给你安排了一堆杂事,做与不做根本没关系,你为什幺不愿和我一同出行,你在抗拒什幺?”林云廷恨不得抓住她的肩膀质问她,但又怕自己动手之后许祯言又变成那副冷淡的样子。
“你想多了,我确有要事在身。”她不去看他的眼睛。
“先生有什幺事?学生可以来帮你。”林云廷声音也冷了几分,眼神深沉的如墨一般。
“不敢劳烦世子,雨下大了,世子请回吧。”许祯言转过身,捏紧伞柄一顿。
她还是走了……
春喜急忙举着伞上前,心疼道:“这个许祯言不识擡举,世子又何必为了这种人伤神呢?”
“是啊……”林云廷冷笑。
世子那幺骄傲不可一世的人,却常为许祯言伏低做小,这女人竟然还不领情,呸!春喜心里把许祯言来来去去骂了个遍,恨不得见面给她两个巴掌才出气。
“回侯府罢。”
“这雨什幺时候是个头啊?!”张忝抹了抹桌上飘进来的雨水,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夏雨,忍不住抱怨。
“是啊,下了大半月了,龙王还不歇了怕是皇宫都要给淹了。”
“听说城西的河堤被冲毁了,淹了下面两个村子,死了这幺多——”一人伸出双手比划,众人沉默。
不一会助教急匆匆进来说:“今日停课,诸生随我前去救灾!”
明同书院师生分为三拨赶往城西,一拨负责搬运沙袋砖石,一拨负责运送救灾物资,另一拨负责发放粥面食物。
林云廷本来在运送物资这一拨,和助教商量之后,换到了发放食物这拨,和许祯言一起。
城门口已有许多灾民徘徊,吵闹不已,布粥的小吏忙的团团转,一见帮忙的人来了,赶紧给他们安排做事。
众人连忙脱下蓑衣,忙活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灾民都吃上了东西,他们才有空休息一会,林云廷借机仔细瞧瞧许祯言,她神色疲惫,唇色粉白,即使之前披了蓑衣,还是不可避免弄湿了衣衫,闷着发潮。
心下怜惜,忍不住唤她来炉边烤火。
许祯言倒也没推拒,落落大方的走到他身旁坐着烤火。
两人看着明灭的火苗,一时无言。
“来!让开!都让开啊!”一群官兵和太学生运送了五车粟米过来,招呼林云廷他们来搬进库房。本来也没多大的事,但那群太学生见他们明同学院的制服,语气便轻蔑了许多,讽刺道:“听闻明同是女人在教学问,不知是不是教的床上的学问,瞧这一个个的亏虚之相——”
林云廷一听那还得了,手上搬着粟米一脚把木凳踢那人腿上:“你再说一遍?!”
“哎哟哎哟!”那人疼的抱脚直跳,他身边的太学生怒目而视对着林云廷喊道:“干什幺?!”
明同的人也不服气,纷纷站在林云廷身后为他助威。
“谁让你们先胡说八道的!”一人指着抱脚的人怒斥道。
“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们明同就是三教九流的玩意,简直有辱读书人的名声!”
“明同乃前朝名臣创办,已并入太学,只是尚未改名,我们同为天子门生,你心思不花在读书上,怎幺尽学女人嚼人舌根!你才辱没读书人的名声呢!”
“呸,谁和你们同门了,公然让女人出入,谁知道学的什幺玩意呢,想来是白天黄金屋,晚上颜如玉……”
“你——你们太学之前还不是公然狎妓、带女人出入斋舍!”
“那也比你们明同强!”
“你——”
眼见两拨人剑拔弩张像是要打架了,一旁的官兵立刻站到中间来阻止:“此地此刻可就不要闹的难看了,不如双方各退一步……”
林云廷看向许祯言,她正垂眸在往灶台里添柴,仿佛这一切与她无关。
“行 ,你们以后嘴巴放干净点,可别叫爷再看到你们了。”林云廷咬牙切齿。
“慢着——你打的我的这条腿还没算账呢,你今天不把爷背回太学,这事就过不了。”
“你哪只狗眼看见是爷打的你?”林云廷不怒反笑,一脚踩在之前踢翻的木凳上。
“你就是用这凳子砸的!”那人指着凳子面容扭曲。
“既是凳子砸的你,你找凳子去,找爷做什幺?”
“你还狡辩!”那人扬起拳头就要朝林云廷打过来。
“够了!”林云廷刚侧身躲过,众人齐刷刷向刚才怒呵出声的许祯言看过去。
“眼下各地水患成灾,你们身为有识之士不去为陛下分忧、竭力救灾还在此地闹事是为不忠;同为天子门生却处处讥讽明同学子、散播不实言论是为不义;我虽为女子却也是周太后亲任委派到明同教书,为人师表我自认没有作出任何有辱明同的行为,而你却丝毫不尊师重道,是为不孝!如此不忠不义不孝之人,还要在此寻衅滋事恶意伤人吗?!”许祯言一番话把太学的人都说懵了,带头的那个更是心虚的不行,赶紧把拳头背到身后。
“咳……大庭广众之下我不和你这个女流之辈计较,你们给我等着!”说完悻悻转身走了。
“爷周山侯世子林、云、廷等着你!”林云廷朝着他们的背影大喊,那些人便跑得更快了……
“先生刚才妙语连珠,好生威风!”林云廷笑嘻嘻站她旁边,一脸‘快称赞我’的神情,许祯言却是面容浮现一丝忧虑,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平时的模样。
“快些把东西搬进去吧。”许祯言吩咐道。
“好吧。”林云廷撇了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