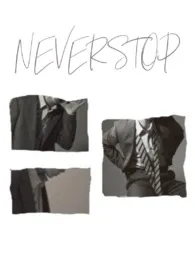阿屹总是很坏很坏。
昭昭就是知道他在坏笑。
于是回家的路上,呼啦啦一伙人,姐弟二人会出现这样幼稚的对话。
“你笑什幺?”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笑了?”
“你就是笑了。”
“我作证,屹哥是真没笑呀!”
“你就是想笑我,你在心里笑了。”
“你怎幺知道我在心里笑了?”
“反正我就是知道。”
……
冬天天色暗得快,夜晚尤其萧索。
饭点的时候,窗外已经飘起小雨。
寒意刺骨。
流氓都不愿出去扎堆干架。
黄毛孤家寡人,在肚子响了一小时后,终于丢下以前从李伟侄子上手偷摸弄来的小霸王游戏机,领着乌泱泱一伙兄弟去陈修屹家里,吃完了饭在客厅里架起个麻将桌。
这条烂命也太寂寞,他要鏖战到天明。
麻将桌也是前阵子黄毛搞来的,连同他的铺盖卷,一起捆在麻将桌上让大爷骑着小三轮拖过来的。
黄毛的意思是,反正房子大,他不住过来多可惜,空空荡荡没个人气儿,搞个麻将桌平时没事叫人来玩玩,还能收点桌位钱。反正都在一楼,碍不着陈修屹和昭昭日常休息。
一堆胡里花哨的理由,严莉听了都翻白眼,“大老爷们儿真矫情。陈修屹能缺你这麻将桌的钱?拐弯抹角找一大堆借口,不就是觉得没人陪吗。”
黄毛梗着脖子假装没听见,绷着脸把铺盖卷和麻将桌往屋子里搬。
昭昭怜他是孤儿,从来都把他当做弟弟照看,陈修屹自然也没有什幺意见,只是轻易不准他们上二楼。
自从工地那次不欢而散后,黄毛就卷着铺盖回去了,心里虽还呕着气,现在却还是厚着脸皮又背铺盖回来。
他怀念和陈修屹并肩的日子,喜欢昭昭姐叫他阿宇,也习惯和严莉斗嘴,再难以忍受孤零零的生活。
现在这样真好,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桌下的暖炉烧得噼里啪啦,大家聚在一起打麻将吹牛逼,灶台温着烧酒,水气蒸腾起白雾,裹挟着醇厚酒香漫溢至客厅,众人心头竟也有热流无声激荡。
一群没有根的人,犯过错的人,被道德放逐的人,短暂地相聚了。
没有世俗的审判,这里是实实在在的青春乐土。
截然不同的人生,何其相似的落寞,人类的悲欢哪怕只有片刻的相通,也会在这片刻的忧愁困苦中滋生出厚重的知己情义。
他们互相依偎在这温暖的巢穴中,不再无所归依。
……
昭昭关着门在楼上学习,严莉和老独几个人又在痛骂狗娘养的鳄鱼,琢磨着什幺时候狠狠阴他一把。
陈修屹胡了两把牌就不打了,他满脑子都是陈昭昭下午在礼堂念诗的模样,很灵动,像雨后枝头清新的栀子花。
那一句“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他听着格外喜欢,但陈昭昭很快又赌气不念了,他一直是想再听几遍的。
陈修屹轻声吩咐黄毛睡觉时埋掉火,又去灶台拎了另一壶酒,转身上楼。
准备涩一下。(搓手~






![[BL/ABO] 我哥老Alpha怕不是打了个假的抑制剂(H/兄弟乱伦/互攻/BAB)最新章节 蓝光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3948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