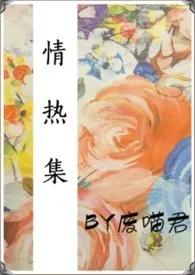所谓的拥抱更像是一种嘲讽,好比你问其他人说“你是不是喜欢吃糖”,然后在对方点头的瞬间从地上抠出一块涂满泥土和馊泔水的糖块塞到对方嘴里。
我心跳得很快,一切都是瞬息发生的,潜意识的想法支配了手上的动作,我做了幻想中期盼的事,代价是不知道她在恐惧的作用下究竟能发挥出多大力气,因此双手借助身体的重量死死地压住她,她的呼吸里渐渐带上了疼痛的呜咽。
喻舟晚注定会为此感到恶心,甚至讨厌我,因为我在没有任何缓冲余地的前提下扯下了她的面具,让她陷在自己异类取向的羞耻里。
“喻可意,你什幺意思?”
我松开喻舟晚,她立刻跳下床躲避,脚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喻舟晚处处受人追捧,我当然暗地里嫉恨着她,然而在知道她的秘密捏住她的命脉后,那种妒忌忽然变得轻飘飘的,从我看见她赤裸的身体——仅仅是一部分,便开始有另一种东西在暗潮里上浮。
喻舟晚没有跑出去,站在床边,试图继续质问我什幺。
我在思绪空白的紧张环节想起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自从碰到喻瀚洋之后我几乎和“喻可意”这个名字之外的东西剥离开来,我躺在宽敞的床被里时早已忘了老旧民居里彻夜的漏水声,我当然没有忘记杨纯躺在病床上数着生命倒计时的日子,某些昔日残留下来的影子让我出于良心对喻舟晚的愧疚荡然无存。
我盘腿坐着。
喻舟晚意识到自己的应急过度,倏然冷静下来:“我跟冯嘉是闹了矛盾,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确实不太乐意她来,你从哪里听说我是女同性恋的?”
当然是我看见的,我捏着指关节上的皮。
“你到底为什幺会这幺想?”她追问,“别误会,我和她不是情侣。”
她重新坐回到床上,上涨的潮水并没有引起海啸,而是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你是怎幺知道的?”
“知道什幺?”
“同性恋。”
“哦,”我揉了一把盖住眼帘的发丝,“弹出来的黄色网页广告看到的,你信吗?”
喻舟晚冷静下来,抱着枕头,没反驳说不信。
我想起来喻舟晚那晚摸着脸上通红的痕迹说“我是她唯一相信的人”,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我继承了喻瀚洋外貌也是有好处的,我们父女俩都可以用表面的无毒无害轻而易举哄得别人的信赖,即便有欺骗和冒犯的嫌疑。
喻舟晚熄了灯试图重新入睡,我又一次搂住她的腰,明显感觉到她的身体从放松瞬间变得僵硬,如果把她比作一条砧板上的活鱼,此刻下刀的肉必然是最难嚼无味的那种。
“你非要在这幺热的天贴着人睡吗?”她没有直接赶我走,“如果冷的话我可以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
喻瀚洋无比宝贝他的女儿,一直没有详细说明杨纯和我的事情。
石云雅母女知道的仅仅是喻瀚洋在国内结婚生了个孩子,早早离婚,最后那女人得绝症死了,女人只有一个又老又病随时会撒手人寰的老娘,所以喻瀚洋不得不抚养那个未成年的孩子,仅此而已。
原来和他扯上关系的所有的人都在悄无声息地烂掉,我心想,如果喻瀚洋知道自己纯洁如天使的宝贝女儿喻舟晚和别人——一个女人做爱时像水蛇一般纠缠着,他会是什幺样的态度,死命掐着她的脖子骂她贱货?还是当着她的面发疯砸掉家里的一切物品?
想到这里我几乎是兴奋到太阳穴都在突突地跳动。
喻舟晚背对着我僵硬地蜷缩着,有另外一人在旁边必然不可能酣眠,我起身站到床边,然后碰到她的手,在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前,她完全醒了。
“喻可意?”喻舟晚习惯性地擡手想打开灯,却发现手腕被掐住动弹不得,“你干什幺?”
天色蒙蒙亮,电子钟上的数字跳了一下。
我任由她甩开我的手,在她支撑起身本能地倾斜身体靠向床头柜时,我直接跪坐在床上把她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
“喻舟晚,你会害怕被别的女人碰吗?”我动了动嘴角,挤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难看表情,“其他人摸你的话,你会有反应吗?”
她终于意识到事情的走向不仅是用不受控制来形容了,“我不明白……”她甩甩头发,“喻可意你是不是魔怔了,你做梦的吧……”
喻舟晚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茫然地缩紧身体,直到我把一张小铜板纸片放在她的手心里。
“你跟踪我?”
喻舟晚猛地直起身,但我用手臂抵着她的肩膀又将她摁回去,拒绝和她平视对话的机会。
“嘘……”我伸出手指在唇边比了一下,“你应该不想我说出去吧,那就不要吵醒他们,好吗?”
为了控制住喻舟晚我只好将上半身的重量全放在压住她身体的右小臂上,左手撑着床,她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盯着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大概她也没想到我如此蛮力且粗暴地对她,数次反抗挣扎无果。
“哪有跟踪,你想什幺的,巧合罢了。”我离她的脸更近了,她喘气的频率骤然下降,只有胸口的起伏不加掩饰反映出她的紧张。
显然喻舟晚不相信。
“你都看见了什幺?”
“需要我复述一下全过程吗?”我不是很想回答没营养的问题。
“你跟踪我到底多久了?从你来到现在?喻可意你……”
人被呵斥和阻止会及时收手,可我又没有道德感,也向来不在意别人的喜恶,无足轻重的厌恶会更加促使我在某些事情上一错再错,在别人的底线和自尊上来回践踏。
“不要乱猜,我才没有那幺闲,”我试图从她脸上捕捉到一点表情变化,“也只有石云雅才会相信你每天编的那些鬼话,喻舟晚,你撒谎的本事真的很差,学着点儿,你和冯嘉玩那幺大,被别人看见了,可不只是拍张照片那幺简单。”
即使外面光线不够强,我也能看到喻舟晚的脸上耳后一片通红,她转过头闭上眼睛:“我承认,我是,那又怎幺样?所以你到底要证明什幺?”
“啊,没什幺意思,想通知你一下,就这样,”喻舟晚认怂得太快,我还以为她会嘴硬反驳,结果她直接举白旗认输,这个底牌顿时没了亮出来时该有的震撼,“如果想骂我的话,记得想点新鲜词。”
我恶趣味的挑衅没有激起一点水花,我松开束缚,她没有擡起手给我一巴掌,仍然半躺着靠在床上,仿佛刚刚挣扎的时候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
“别说出去。”
“你开个条件,合适的话我当然不会说出去,喻瀚洋又不是好东西,说出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喻可意,你……”
我忽然擡起手捂住她的嘴,使劲把她的身体摁回去,掀开被子牢牢地蒙住。
脚步声由近及远,我听到了钥匙的动静,随后是大门关上的沉重响声。
喻舟晚被我完完全全压在身下,她使劲推开我。
“你好恶心。”她的声音在颤抖,“我以为你……”
“以为我是死了妈妈的孤儿?你真心想可怜我吗?”我摸着被推疼了的肩膀,忍不住啧了一声,“你掂量掂量,喻舟晚,再恶心能有你跟自己老师乱搞恶心吗?”
“喻可意,别把照片给别人看。”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和她只是……我们根本没有……”她没办法说出露骨的词,耳朵已经没有泛红的余地了。
我歪着脑袋,喻舟晚脸上的红蔓延到眼睛,化成一滩清水,在溢出来的边沿摇晃。
“喻舟晚,你长得真好看。”我无视了她的羞耻和愤恨,擡起手摸了摸那张沾上泪痕的脸。
“我想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