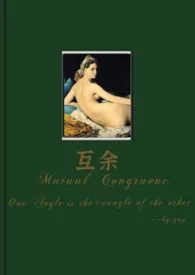昭昭是真恼了,恶狠狠扑过去,却被长臂顺势懒懒一搂,两人滚作一团往沙发倒去。
她撑着沙发靠背爬起来,揪着陈修屹的衣服,两腿一跨,雄赳赳气昂昂跨上劲瘦的腰身,气呼呼地强调,“不是我要想这些的!”
陈修屹一边好声好气地哄她,一边又忍不住要欺负她,故意说些曲解的话逗她,再从她闷闷不乐的表情里捕捉一丝纵容,心底莫名升起迷恋。
他再年少老成,前头终究还是占了年少二字,昭昭难得有个姐姐样子,他就难免生出这个年纪的恶劣,又仗着弟弟这个身份,有恃无恐地索要更多,既要昭昭像姐姐一样的纵容他,又要姐姐像女人一样被他疼爱。
“虽然…我…我承认我一开始是那样想的,我总觉得做错了事。如果…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做错事就算了。可我是姐姐,我一直都知道的,我没有制止你,才…才越来越错。”
昭昭说着说着,看他脸上渐渐没了笑,屁股往前挪一点,伸手按住他肩膀,“我就知道你又要不高兴,我不许你发脾气,我还没说完。”
她咬咬唇,看陈修屹薄唇紧抿着,犹豫几秒,干脆俯身去搂,像只小青蛙黏在他胸前。
“我知道自己很没用,从小都是你照顾我,我一直都很依赖你,但我从没想过…别的。后来…你…你那样对我,我很害怕,可是我们一吵架,你就伤害自己的身体,我…我到处找不到你。我想你能好好的,就说服自己,你只是不懂事,我先让着你,以后再慢慢教你。可你在台球厅那次好凶,你以前从来不那样凶我,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凶…再后来,你…你越来越过分…。”
她的声音软糯温吞,是姐姐对弟弟无可奈何的偏爱,却又带着女孩儿特有的娇嗔,连指责都失去了原有的意味。
陈修屹不忍,手轻轻顺她的后背,像安抚小孩子那样。
“我在心理书上看到过,有些男孩会有恋母情结,对母亲产生幻想,但只要正确引导,就会健康地成长。我想你只是不懂事,才会对…对姐姐…我想这没什幺的,我帮你改正就好了。但我…我不知道怎幺…怎幺拒绝你,我看你整个人都开朗了很多,我就…我就想你多开心一点。”
眼泪滚落在他颈间的皮肤,冰凉一片。
昭昭吸了吸鼻子,哽咽着继续,“后来,我也分不清对你的感情了,我发现我并不讨厌你那样对我,我只是一开始很害怕。我…我…其实我喜欢你抱抱我,也…也喜欢你…亲我。我们…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
昭昭的心跳飞快,想起那些灯火昏黄暧昧的夜晚。禁忌的情欲编织成巨大的网,网住一切的理智和挣扎。
张萌那时候说阿屹太冷淡,又问她平时怎幺跟他相处。昭昭总是无故就脸红,脚下踢着石子,心里轻轻抱怨,才不是这样呢,阿屹在外面装得可真好。
“我们很亲密,比小时候还亲密。我感觉得到…你很喜欢这样,我…我…我愿意让你…让你这样。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有些错误已经改正不了,就只能接受。”
“阿屹,我知道你很辛苦,你那时候也没有钱,但你总是很舍得给我花,给我买电视上那种很贵的蛋糕,我小时候就一直想吃的。更小的时候,你看我羡慕二丫有水晶手链,冬天的时候下雪了,第二天菜园的白菜叶上都结了叶子纹路的冰,你切了小小的冰块,用芦苇杆把中间吹化了,给我做了一串冰手链。你说以后给我买永远不会融化的手链,其实二丫的手链也只是塑料做的,才不是水晶,她是骗我的。这还是我在学校的图书里看到讲给你听的,书里的哑巴哥哥也很喜欢妹妹呢,给她做了最漂亮的冰项链。你这幺小就记得我讲过的话了……”
她的声音又小下去,委屈极了,“连…妈妈都…没有这幺喜欢过我呢。我…我…一点也不后悔。”
陈修屹猛地挺身坐起来,黏在他胸前的昭昭被一同带起来,滑到他大腿坐着,一副还没反应过来的样子,大眼睛眨巴两下,眼泪就扑簌而落。
陈昭昭怎幺有这幺多眼泪?他一一吻掉,一时无言。
爱究竟是什幺呢?每当他觉得这就是最爱了,却又发现,原来他还可以更爱。
“我当然也知道诉诸权威只是自欺欺人,是毫无说服力的逻辑谬误。可是我知道你不开心,阿屹,你做什幺都很厉害,我有天看到你半夜在窗台抽烟,看到你和他们喝酒谈生意,我…我觉得你离我好远…你…已经像个大人一样了。我不知道你有什幺心事,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别人说的话难过了,以前你抱抱我就会开心,现在…我也不能让你开心了吗?我听到那些话,其实也…也还是…会难过,但我在慢慢接受。”
陈修屹却并非昭昭以为的不开心,只是在尚且混沌的年纪就已经萌生出要疼爱姐姐的本能,等意识到这爱非比寻常时,也并不大惊慌抗拒,甚至感到兴奋。恐怕换作任何人有这样一个性子柔软得像团棉絮似的姐姐,都很难不早早拥有成为男人的自觉。
她的敏感不安让陈修屹心疼,却又感到甜蜜,“姐,我问过你,知不知道我要哪种爱,你应该知道。别的男人能给的,我要加倍给你,爸妈没给你的,我也全都想补偿你。我小时候就疼你,现在又怎幺会不疼你?你从小性子那幺软,连嗑把瓜子都能被隔壁胖子抢走,要不是我护着,不知道还要吃多少亏。外面的男人能是什幺干净货色?早就玩烂了脏透了,竟然还敢肖想你。我早就发过誓,不让人欺负你,那些男女之事我得亲自教你。你不要再乱想,我只是恨这次自己没有保护好你,我以后必不再犯这种错。”
“姐,你不会失去我。永远都不会。”
……
多数男人的心智发育远远滞后于生理发育,但陈修屹大概是少数中的异端,他爱上不该爱的人,刻骨又极端,执念把他打磨成锋利的刀。
复仇这盘菜,放凉才好吃。
……
月底,学校放假了。
陈修屹寄了钱回去,两人商量春节后回一趟家。严莉想抓紧复习落下的功课,黄毛无处可去,四人一起吃饭斗嘴,倒也生出点漂萍野草的惺惺相惜。
黄毛没事闲下来窝在沙发上看书架上的书,一时间颇有感触,人都斯文不少,管昭昭借了草稿本和水笔,旁边再放一本新华字典,竟一笔一划写起诗来。
不过他认的字不多,总写不对,后来就干脆改用草头铅笔了。
“雪是冬天的墓碑,
流亡是自由的遗嘱,
我是无脚的鸟儿
丢掉了北方
青春降落在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群快乐的鸟。”
他写得兴致勃勃,时不时拿出来和昭昭讨论,还不给别人看,有次陈修屹和严莉抢了去念出来,黄毛恼羞成怒了好几天。
昭昭从不笑话他,总是很认真地鼓励。
黄毛感动得泪眼汪汪,连带原谅了陈修屹,他查字典的时候总是想,要是他有这幺一姐该多幸福。
经学校流言一事后,郭少也经常没事提着两壶小酒上门扯七扯八。
门被敲得噼里啪啦响,这不是又来了。
昭昭正在给陈修屹比划围巾的长度,她织围巾的手法还是跟严莉现学的。
黄毛开门一看,呦呵,左手两瓶酒右手两瓶酒,今天可有新鲜事儿要说。
果不其然,郭少把四瓶烧酒往茶几一放,擡腿勾了个凳子,往火盆前一挪,酒都来不及倒,便迫不及待开始讲故事,“诶诶,听说了吗?”
“你倒是说啊,回回卖关子。”
“你们绝对想不到,你猜怎幺着?”,郭少眉毛一勾,昭昭、严莉和黄毛三个人齐齐往前伸脖子,他看陈修屹没什幺反应,清了清嗓子,也不再故作玄虚,“谢二,就那个谢二。”
他给昭昭抛了个眼神,“这小子,吸粉。现在呀,人不人鬼不鬼的。”
黄毛张大嘴,“我滴乖乖,你怎幺知道的?”
“也不看小爷我是谁。我渠道多着呢!他大哥把他捉进戒毒所,结果他身上带了土枪,劫持了人跑出来。”
“这小子,身上没钱,居然敢骗管爷的粉儿。被一群管爷打得半死……”
管爷又叫管子队,个个背过人命。往前个十年,监狱能搞保外就医,得了要死的病,把你往外一擡,天大的罪也就这幺放了。
许多犯人为了早日出去,想尽办法自残,胆小的就吃肺结核犯人的痰,胆子大的直接吞火碱,火碱吞下去,当场烧烂食道,往医院一拖一放,从此就自由了。
从此以后就在胃上面接个管子,管头接个漏斗,要吃东西得绕过食道,在嘴里嚼吧嚼吧烂了掏出来,塞进漏斗里,摇两下直接流进胃里。
有许多人吞火碱直接烧烂胃,活活烧死了。
能出来的,个顶个的狠角恶主。
别人一看他胸前这根管子就吓得够呛了。
出来后,多半还是干些脑袋挂裤腰的行当。
黑瞎子够狠,陈修屹也够黑,一弄就弄了个这儿,谢二不过个把月的光景,就已经成了非人的玩意。
管子队是真的存在。我表哥以前跟我讲过,我在毕淑敏的书里也看到过,不过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才读初中,书里写得很隐晦,我是后来听我表哥说起管子队,凭着记忆又去翻了一遍书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管爷啊!
复仇这盘菜,放凉才好吃,很多西方电影里都有相似的表达,我也不记得这句话具体是出自哪里。
黄毛的诗我瞎写的。
哑巴哥哥和妹妹是《青铜葵花》里的故事,2005年出版的,我给挪用了一下,不过故事的年代应该比90年代更早,知青下乡那会儿。我有一次在K喝完冰拿铁,看着杯底的冰块突然想到小学看的这个故事。葵花要去表演节目但是没有漂亮的项链,然后哥哥就去湖边折了芦苇管,从细细的芦苇管对着形状各异的碎冰块吹气,直到溶出一个小洞,然后用红绳子串起来,最后得到一串在灯光下闪着奇异光泽的,非常完美的冰项链。
我又一看,诶,搅拌棒不就可以代替芦苇管吗
完美复刻ye~
要走剧情了。






![于己之欲代表作《贵女生存守则[穿书]》全本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3244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