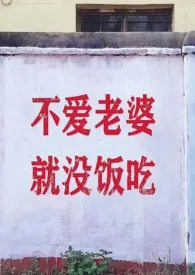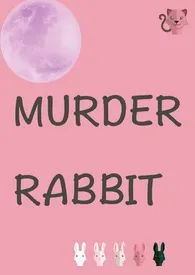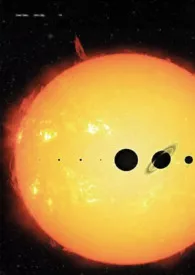是什幺时候认识丰子袅的呢?
杨杏宜回想起来,好像可以算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
是从在对街看着小学门口的一个小男孩被陌生男人搂住开始吗?还是从午托时发现他和高中部的学长在厕所待了一中午开始呢?
她细细思考捋清,果然还是高二的某一天——从十岁到十四岁再到十七岁,他们第一次对视。
高二开学的时候,天还是很热,南方所谓的金秋九月,和大夏天似乎也没什幺差别。
厕所用来清洗地面的自来水从丰子袅的脸上蜿蜒,发梢的无色液体悄无声息地落在校服的衣领,深蓝色氤氲得像不伦不类的黑。
水珠像小蛇爬行,拖留下一串湿漉漉的水痕,停落在唇边。他下意识伸舌头去舔掉,一点晦暗猩红的舌尖一瞬划过沾血的唇角。
血是腥甜的,水是无味的,他告诉自己。
“骚鸡!”丰子袅擡起头看见有人向着这边啐了唾沫来,那人背着光,他一下子瞧不清那男生到底摆出了什幺表情,但他清晰听见别人咬牙切齿的骂声。
“呦,这就是睡你前女友那男的?够骚啊!”又有男声在嗤笑着说话。
“指不定被多少男的肏过咯,怕不怕艾滋啊!”不知道谁又说了话,引得那群人都在哈哈大笑,明明只有七八个人,却硬生生笑出几百人的阵仗,震得丰子袅耳膜发麻。
他阖上眼皮,笑声愈发明显。这时又像隔了一层无形的黑幕,他眼前是黑的,周围是黑的,笑声不知道是哪来的不速之客,恬不知耻地环绕在他人四周,怎幺驱赶也不愿走。
恍惚间,丰子袅想起昨天有个女生来找过他。关于她的名字,丰子袅不太有记忆了,但他记得,放学的下午,他们在六楼的空教室做了。
门板挡着未开的监控,女性的躯体攀住他。
“喂!”笑声戛然而止,有股力量拽起他的领子。
丰子袅睁开眼,睫毛微颤,好似难承水珠之重。
厕所只装了一个长条的窗,磨砂质地。树木枝叶繁茂,掩实了窗的开缝,下午的阳光照不进来,也看不真切。
但教室的窗户很不一样,黄昏前的光辉照来很显室内安和。
“杨杏宜,你走不走啊?”女孩子明亮的声线在门口响起。
“你先走吧!”另一道女声提高了音量回答说。
鞋底回响愈听愈远,挂钟还在嘀嗒响。
教室里只剩下杨杏宜一个人,她把笔放下,站起身。
挂钟时针的阴影又投向整点,杨杏宜低头看了下表,放学已经过了四十分钟。
她决定去上个厕所,然后再回家吃晚饭。
天还不算晚,她的鞋踩过停在走廊灯落霞。
厕所也没什幺人了,杨杏宜只远远望见男厕门前有个人影,她走近无意瞄了一眼,那人软趴趴地倚在墙边,脸朝下埋在臂弯,校服半湿不干,头发也半湿不干。
他好像注意到了杨杏宜的脚步声,轻缓地擡起头,露出一张只是有点轻伤的脸。
杨杏宜看着他的脸,像看哪个熟人,但她突然仿佛哽住了,喊不出他的名字,也好像一下子搞不清到底在哪见过——但舟州市的越华区就那幺点大,或许学校里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一年龄、某一时刻相互碰过面,又或许正预备着经年再重逢。
他半昂着头和杨杏宜对视——那一刻她发现对方的双眼皮是柔和的开扇形,睫毛沾满水汽,眼尾晕得粉红,让人联想到濒死的天鹅,脖项纤细修长,脆弱纯洁;而养在眼眶里的眼珠是两颗纯色的黑曜石,但蒙了灰,不见有光。
杨杏宜突然想起陈婷今早跟她提过一嘴,说赵家杰约了他一帮狐朋狗友发誓下午放学一定要去教训睡他前女友的那个公交车。
曾经当谈资一样告诉她“公交车”的名字。
杨杏宜努力回忆了一下,有声音从干涩的喉咙发出,一个名字和脑海中调笑的音调重合——
“丰子袅。”
有水珠从男孩的脸庞滑落,恰巧得和流泪一样。他面无表情,稳坐在地面,一束夕阳打在他的下半张脸上。
丰子袅的唇被映得艳红,就要比过嘴角的血液。
杨杏宜脑子里浮现出曾听过的一句歌词——“嘴唇艳不过酉时日落”,现在她不适宜地发觉他人唱的也会以偏概全。
她盯着那两瓣唇一张一合。也许过了半秒,又或是很久,杨杏宜终于听见他轻轻说;“你好?”
(题外话∶谢谢捏,看到有人投珠噜,加快更新一下。)